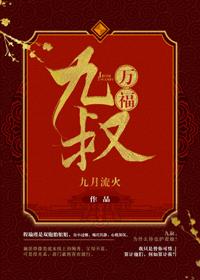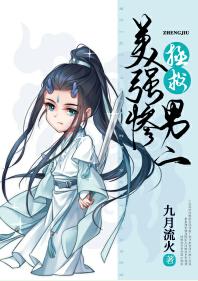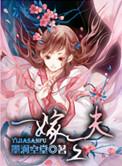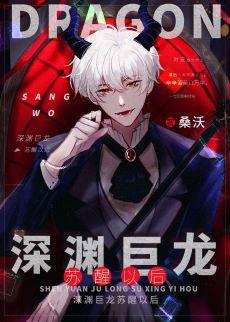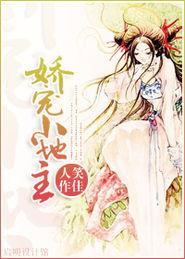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4)(3 / 5)
内兮归故乡”的往事,通篇模拟他家乡一位农夫的口吻,对当年无赖、今日皇帝刘邦的威仪,冷眼旁观,热讽冷刺,写得俏皮泼辣,活灵活现,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换了姓,叫什么汉高祖!”出了问题,“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只因这一句话,把通篇的历史感破坏殆尽。此类纰漏在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发现,恕不举例,因为我的用意并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这样的错误。这当然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张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颠倒、语焉不详等种种现象,需要反复地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纠谬勘误、拾遗补缺,而由于香港长期处在港英统治下,有关抗英斗争的史料则大量湮没,需要深人民间走访寻觅,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许多同胞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协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大量创作素材,特别是埋没在民间的关于抗英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资料,那是在图书馆、档案馆都找不到的,因而更加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将曾经帮助过我的同胞们、朋友们的名字列出,一一鸣谢,因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些为我带路的好心人,帮我查找资料的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难以开列齐全,但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辩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又决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这便是创作者最难解决的难题。在本书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凡采用真实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据,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对读者负责,不能愧对历史,失信于读者,写出每一个字都觉得手中的笔很沉重。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任何史料都只是历史遗留的部分痕迹,而不是全部。即使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并且运用多种手段有意识地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实物资料的历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对历史的求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永远不能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辩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又决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这便是创作者最难解决的难题。在本书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凡采用真实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据,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对读者负责,不能愧对历史,失信于读者,写出每一个字都觉得手中的笔很沉重。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任何史料都只是历史遗留的部分痕迹,而不是全部。即使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并且运用多种手段有意识地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实物资料的历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对历史的求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永远不能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夜的命名术
- 蓝与紫的霓虹中,浓密的钢铁苍穹下,数据洪流的前端,是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也是现实与虚幻的分界。钢铁与身体,过去与未来。这里,表世界与里世界并存,面前的一切,像是时间之墙近在眼前。黑暗逐渐笼罩。可你要明白啊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要用火。
- 05-19
- 九叔万福
- 文案: 程瑜瑾是双胞胎姐姐,本来定下一门极好的亲事。可是后来她知道,未婚夫靖勇侯之所以提亲是误把她认成妹妹。靖勇侯和妹妹虐恋情深,分分合合,最后才终于冲破阻力在一起。而程瑜瑾就是那个顶替妹妹的大好姻缘,不停陷害妹妹,阻碍有情人在一起的恶毒姐姐兼前妻...
- 04-21
- 拯救美强惨男二
- 文案: 洛晗看了一本人人恋爱脑、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仙侠小说,之后被召唤穿书,得知原来她是小说里的天道化身。 小说后期,主角们为了爱发动战争,差点毁灭世界。她为了自救,只好走上拯救世界之路。想要制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黑化男二掰回来。 男二凌清宵是...
- 04-21
- 一嫁三夫
- 算命的道士说,江家只能娶一个媳妇。但江家一共有三个兄弟,这媳妇怎么分呢?谁娶?剩下两个当一辈子光棍?老大摸了摸下巴:要不,我们凑合着用一个? PS.穿越古代,和三兄弟一起的种田生活,无虐,有肉。 第一章 清晨。元皓推开破旧的木板门,望着门...
- 08-22
- 深渊巨龙苏醒以后
- 文案: 时安是世界上最后一条深渊巨龙。 由于太过无聊,所以他抱着自己的财宝,愉快地陷入了沉睡。 五万年之后,时安心满意足地睁开双眼。 ——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手短脚短的弱小人形。 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莫名其妙缩小的身体,又抬头环视了一圈自己空空荡荡的洞穴:...
- 04-13
- 娇宠小地主
- 昌平县最热闹的醉月楼。 噜噜站在高处,茫然地望着下面的一个个雄性。 他们都在仰头看她,看她的同伴啾啾。他们眼里,是雄性看到猎物时才会闪烁的兴奋光芒,他们脸上,是神秘莫测的笑容。她不懂他们身上穿的东西,他们身边弄成奇怪形状的一块块儿木头,他们...
- 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