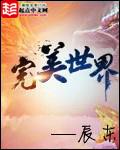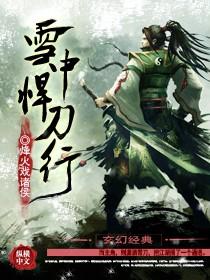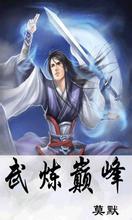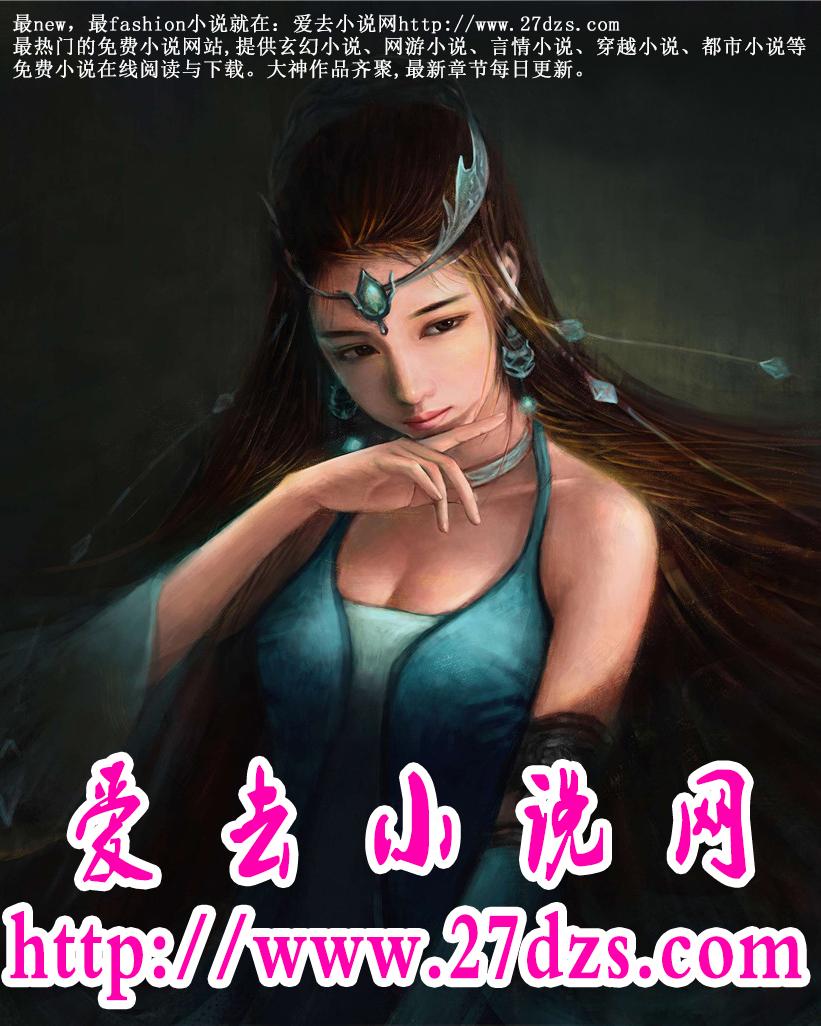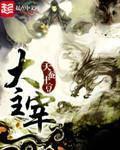第九章 “我回来了” (1)(3 / 22)
得活灵活现,我想也不必再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先生们在搞什么了。愿他们成功。上帝,人类又一次从您那里偷下了天火。”盖达尔说。
“盖达尔,我们没有什么要忏悔的。该忏悔的是日本人,是他们先动了手,而且几乎把我们打懵了。他们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我们必须加紧干!”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的哲学也是地道的英国式的: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老惠特尼举起酒杯:“为B—29的成功干杯!”
机群掠过厂区,发动机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槟酒酒面泛起涟漪。
“可爱的B—29!”盖达尔先生轻轻说。
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证明了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惊人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轰炸机在三十年的时间中孵化,出壳,长大,成熟,同汽车、轮船、无线电设备一样日臻完善,显示了人类在技术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艺。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挥的早期战略轰炸机群,包括“齐柏林”巨型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就从比利时越海轰炸英伦。英军还以牙眼,多伦上校指挥汉达尔贝奇轰炸机队猛袭德国工业城市,投弹五百四十吨。这时候,一个南非佬扬·史默兹将军想象出战略轰炸的远景:“它将凭着破坏敌国大规模的产业中心和人口众多的都市,使之丧失战争能力和士气,从而扮演起战争的主角……而旧式的海、陆军作战,将沦为次要的,或是辅助性的战斗。”
任何幻想都包含着不切实际的迷雾,都受到现实和守旧者的指谪。这也难怪,人类的惰性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曰“反馈”。否则,人类早在电子学中说的那个“自激振荡”中毁掉了。
然而确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从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频率,在明智的决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荡。当初,一位三十六岁的美国陆军准将威廉“比利”·米切尔,在他身为美军驻法国远征军航空队司令官的时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大空军”。
革新思想在战时就被埋没在世俗见解的泥沙中,战后,更是污积垢沉,无人问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惊人之举,把缴获的几艘德国军舰,开向切萨皮克湾,然后用他自己陆军航空队的马丁式轰炸机把它们一一炸沉。舆论大哗。起码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盖达尔,我们没有什么要忏悔的。该忏悔的是日本人,是他们先动了手,而且几乎把我们打懵了。他们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我们必须加紧干!”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的哲学也是地道的英国式的: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老惠特尼举起酒杯:“为B—29的成功干杯!”
机群掠过厂区,发动机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槟酒酒面泛起涟漪。
“可爱的B—29!”盖达尔先生轻轻说。
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证明了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惊人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轰炸机在三十年的时间中孵化,出壳,长大,成熟,同汽车、轮船、无线电设备一样日臻完善,显示了人类在技术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艺。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挥的早期战略轰炸机群,包括“齐柏林”巨型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就从比利时越海轰炸英伦。英军还以牙眼,多伦上校指挥汉达尔贝奇轰炸机队猛袭德国工业城市,投弹五百四十吨。这时候,一个南非佬扬·史默兹将军想象出战略轰炸的远景:“它将凭着破坏敌国大规模的产业中心和人口众多的都市,使之丧失战争能力和士气,从而扮演起战争的主角……而旧式的海、陆军作战,将沦为次要的,或是辅助性的战斗。”
任何幻想都包含着不切实际的迷雾,都受到现实和守旧者的指谪。这也难怪,人类的惰性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曰“反馈”。否则,人类早在电子学中说的那个“自激振荡”中毁掉了。
然而确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从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频率,在明智的决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荡。当初,一位三十六岁的美国陆军准将威廉“比利”·米切尔,在他身为美军驻法国远征军航空队司令官的时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大空军”。
革新思想在战时就被埋没在世俗见解的泥沙中,战后,更是污积垢沉,无人问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惊人之举,把缴获的几艘德国军舰,开向切萨皮克湾,然后用他自己陆军航空队的马丁式轰炸机把它们一一炸沉。舆论大哗。起码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完美世界
- 一粒尘可填海,一根草斩尽日月星辰,弹指间天翻地覆。 群雄并起,万族林立,诸圣争霸,乱天动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个少年从大荒中走出,一切从这里开始……
- 09-02
- 雪中悍刀行
- 江湖是一张珠帘。 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 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 06-02
- 全球高武
- 今日头条—— “大马宗师突破九品,征战全球!” “小马宗师问鼎至高,横扫欧亚!” “乔帮主再次出手,疑似九品大宗师境!” “股神宝刀未老,全球宗师榜再入前十!” “……” 看着一条条新闻闪现,方平心好累,这剧本不对啊! 各...
- 08-09
- 武炼巅峰
- 武之巅峰,是孤独,是寂寞,是漫漫求索,是高处不胜寒 逆境中成长,绝地里求生,不屈不饶,才能堪破武之极道。 凌霄阁试炼弟子兼扫地小厮杨开偶获一本无字黑书,从此踏上漫漫武道。
- 05-20
- 完美奴隶手记
- 六点整,莫陌准时睁开双眼,关上闹表,眼神中没有一丝迷茫。 洗漱、整理房间、做早饭,一切表现地像个完美的居家男人,除了……浑身赤裸。 阳光透过外层的薄纱窗帘打进来,映出完美的身体曲线。 笔直有力的双腿,窄胯翘臀,柔韧的腰身, 笔挺的脊...
- 07-02
- 大主宰
- 大千世界,位面交汇,万族林立,群雄荟萃,一位位来自下位面的天之至尊,在这无尽世界,演绎着令人向往的传奇,追求着那主宰之路。 无尽火域,炎帝执掌,万火焚苍穹。 武境之内,武祖之威,震慑乾坤。 西天之殿,百战之皇,战威无可敌。 北荒之丘,万墓之地,不死之主...
- 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