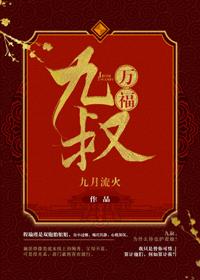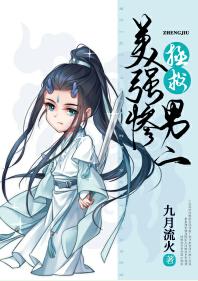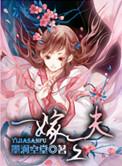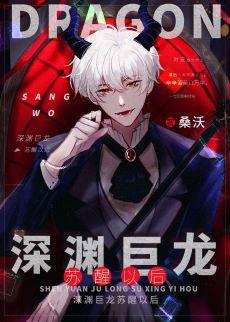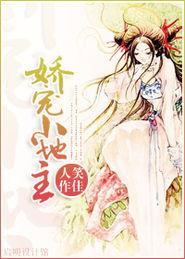第十四章 追随者(3 / 21)
子,何况叔叔已经受了牵连,即使他们想照顾那个男孩,也只能让同样还是小孩子的柳絮出面。的确,没有人会把一个不懂政治的孩子怎么样。
柳絮来到男孩身边,她理解他的哭泣——那哭声里充满了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他可能刚刚体验到在漆黑的夜晚家里凌乱一片、亲人不知去向的局面,这种恐惧是油然而生的。经历过数次家庭变故的柳絮已经克服了这种恐惧,她站在罗家幽暗的院子里,想给哭泣的男孩一点安慰,想以自己的微弱之躯给他一点点微弱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她在黑暗中伸出稚嫩的手指抹去男孩脸上的泪水,将柳条篮子递给他。
男孩没有接篮子。他看着站在眼前的比他高出一头的女孩朦胧的身影,似乎找到了某种安全感。他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哭泣。
柳絮说:“这是新煮的土豆,你饿了吧?”
男孩说:“我不饿,我害怕。”
柳絮说:“怕什么?听说现在砂城比这里闹得还厉害,不仅大人要拉出去斗,小孩子也要陪斗的。”
男孩说:“我怕他们再也不回来了,我怕漆黑的夜晚独自待在家里。”
柳絮说:“不怕,我留在这里陪你。你们家的灯呢?怎么不开灯啊?”
男孩说:“昨晚灯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换下坏灯泡就被带走了。”
男孩说的“他们”是指此刻还没有回家的父母。
许多年里,柳絮常常沉浸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夜深了,男孩的父母没有回来,十一岁的柳絮坚守自己的诺言,留在那个漆黑的院子里陪男孩。他们相拥着靠坐在一棵冰冷的槐树下睡着了,一直睡到旭日东升。然后她看着他醒来。他叫了她一声姐姐。也许,她心里对他产生的朦胧爱意就是在他睁开眼睛叫她姐姐的那一刻萌发的。
后来男孩的母亲回来了,他的父亲罗新宇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叔叔柳馆长则留在县城里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某天,自叔叔遭受批斗以来就一言不发的婶婶突然不知去向,无人照顾的柳絮只好回到乡下祖母家里——离砂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叫艋县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叫沙湖村的偏僻村庄。罗家男孩以及被“赦免”了的男孩的母亲也去了那里,他们由此知晓了一个由动词描述的新事物——下放。也就是说,罗家母子这一去就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了。此时已经到了“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
从艋县的字面意思理解,这里应该是有很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柳絮来到男孩身边,她理解他的哭泣——那哭声里充满了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他可能刚刚体验到在漆黑的夜晚家里凌乱一片、亲人不知去向的局面,这种恐惧是油然而生的。经历过数次家庭变故的柳絮已经克服了这种恐惧,她站在罗家幽暗的院子里,想给哭泣的男孩一点安慰,想以自己的微弱之躯给他一点点微弱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她在黑暗中伸出稚嫩的手指抹去男孩脸上的泪水,将柳条篮子递给他。
男孩没有接篮子。他看着站在眼前的比他高出一头的女孩朦胧的身影,似乎找到了某种安全感。他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哭泣。
柳絮说:“这是新煮的土豆,你饿了吧?”
男孩说:“我不饿,我害怕。”
柳絮说:“怕什么?听说现在砂城比这里闹得还厉害,不仅大人要拉出去斗,小孩子也要陪斗的。”
男孩说:“我怕他们再也不回来了,我怕漆黑的夜晚独自待在家里。”
柳絮说:“不怕,我留在这里陪你。你们家的灯呢?怎么不开灯啊?”
男孩说:“昨晚灯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换下坏灯泡就被带走了。”
男孩说的“他们”是指此刻还没有回家的父母。
许多年里,柳絮常常沉浸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夜深了,男孩的父母没有回来,十一岁的柳絮坚守自己的诺言,留在那个漆黑的院子里陪男孩。他们相拥着靠坐在一棵冰冷的槐树下睡着了,一直睡到旭日东升。然后她看着他醒来。他叫了她一声姐姐。也许,她心里对他产生的朦胧爱意就是在他睁开眼睛叫她姐姐的那一刻萌发的。
后来男孩的母亲回来了,他的父亲罗新宇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叔叔柳馆长则留在县城里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某天,自叔叔遭受批斗以来就一言不发的婶婶突然不知去向,无人照顾的柳絮只好回到乡下祖母家里——离砂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叫艋县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叫沙湖村的偏僻村庄。罗家男孩以及被“赦免”了的男孩的母亲也去了那里,他们由此知晓了一个由动词描述的新事物——下放。也就是说,罗家母子这一去就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了。此时已经到了“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
从艋县的字面意思理解,这里应该是有很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夜的命名术
- 蓝与紫的霓虹中,浓密的钢铁苍穹下,数据洪流的前端,是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也是现实与虚幻的分界。钢铁与身体,过去与未来。这里,表世界与里世界并存,面前的一切,像是时间之墙近在眼前。黑暗逐渐笼罩。可你要明白啊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要用火。
- 05-19
- 九叔万福
- 文案: 程瑜瑾是双胞胎姐姐,本来定下一门极好的亲事。可是后来她知道,未婚夫靖勇侯之所以提亲是误把她认成妹妹。靖勇侯和妹妹虐恋情深,分分合合,最后才终于冲破阻力在一起。而程瑜瑾就是那个顶替妹妹的大好姻缘,不停陷害妹妹,阻碍有情人在一起的恶毒姐姐兼前妻...
- 04-21
- 拯救美强惨男二
- 文案: 洛晗看了一本人人恋爱脑、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仙侠小说,之后被召唤穿书,得知原来她是小说里的天道化身。 小说后期,主角们为了爱发动战争,差点毁灭世界。她为了自救,只好走上拯救世界之路。想要制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黑化男二掰回来。 男二凌清宵是...
- 04-21
- 一嫁三夫
- 算命的道士说,江家只能娶一个媳妇。但江家一共有三个兄弟,这媳妇怎么分呢?谁娶?剩下两个当一辈子光棍?老大摸了摸下巴:要不,我们凑合着用一个? PS.穿越古代,和三兄弟一起的种田生活,无虐,有肉。 第一章 清晨。元皓推开破旧的木板门,望着门...
- 08-22
- 深渊巨龙苏醒以后
- 文案: 时安是世界上最后一条深渊巨龙。 由于太过无聊,所以他抱着自己的财宝,愉快地陷入了沉睡。 五万年之后,时安心满意足地睁开双眼。 ——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手短脚短的弱小人形。 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莫名其妙缩小的身体,又抬头环视了一圈自己空空荡荡的洞穴:...
- 04-13
- 娇宠小地主
- 昌平县最热闹的醉月楼。 噜噜站在高处,茫然地望着下面的一个个雄性。 他们都在仰头看她,看她的同伴啾啾。他们眼里,是雄性看到猎物时才会闪烁的兴奋光芒,他们脸上,是神秘莫测的笑容。她不懂他们身上穿的东西,他们身边弄成奇怪形状的一块块儿木头,他们...
- 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