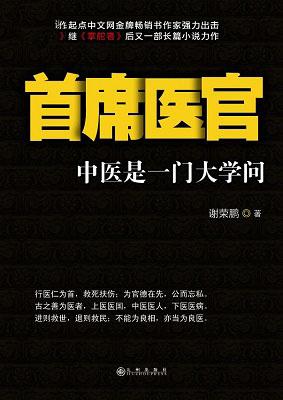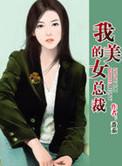第 9 部分(5 / 6)
,有约3/4投票支持杜鲁门。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工会在使民主党成为美国主导政党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尔·罗杰斯那句有名的调侃:“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党人。”以此来形容“新政”之前与现在的民主党,可谓公允,但在当年劳工组织势力强大的时候,这句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当时的工会为民主党准备了现成的组织架构,工会不仅是竞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且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队助选常备军,助选员们分发草坪标牌,向车身粘贴标记、传单,逐门逐户地拉票,并在选举日动员选民出门投票。在那个年代,电视竞选尚未成为主要的竞选方式,这些帮助就显得更加重要。
强大的工会运动还有一个较为微妙但也许同样重要的后果,即对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觉悟与投票参与率的影响。那些密切关注政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淡漠态度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当然这种淡漠是有原因的,虽说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单个选民的决定却几乎无关大局。因此,忙着工作、养育子女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动力紧密关注政界的角逐。这一理性的冷漠态度使政治进程产生了上行的阶层偏向: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相比,收入较高者关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结果是,选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家在设计政策时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
但工会有着削弱这一阶层偏向的效果,工会明确呼吁其成员投票。也许更重要的是,工会会议上的政治讨论、工会成员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会提高工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当他们与配偶、朋友、家人等谈论时,还会提高后者的觉悟。由于人们喜欢与收入相当者交往,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劳动力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与1964年一样高,在收入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将会多出10%,而收入较高的1/3只会多出3%。所以,工会运动的力量让美国政治的经济重心下移,这让民主党人获益良多。
总之,与之前的“长镀金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态势大大有利于实施促进收入均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激进举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国家的人反而被当成怪物。无选举权的移民劳工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阶层;南方有条件地暂时支持经济平等,只要这不转化为种族平等;强大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工会在使民主党成为美国主导政党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尔·罗杰斯那句有名的调侃:“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党人。”以此来形容“新政”之前与现在的民主党,可谓公允,但在当年劳工组织势力强大的时候,这句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当时的工会为民主党准备了现成的组织架构,工会不仅是竞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且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队助选常备军,助选员们分发草坪标牌,向车身粘贴标记、传单,逐门逐户地拉票,并在选举日动员选民出门投票。在那个年代,电视竞选尚未成为主要的竞选方式,这些帮助就显得更加重要。
强大的工会运动还有一个较为微妙但也许同样重要的后果,即对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觉悟与投票参与率的影响。那些密切关注政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淡漠态度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当然这种淡漠是有原因的,虽说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单个选民的决定却几乎无关大局。因此,忙着工作、养育子女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动力紧密关注政界的角逐。这一理性的冷漠态度使政治进程产生了上行的阶层偏向: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相比,收入较高者关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结果是,选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家在设计政策时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
但工会有着削弱这一阶层偏向的效果,工会明确呼吁其成员投票。也许更重要的是,工会会议上的政治讨论、工会成员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会提高工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当他们与配偶、朋友、家人等谈论时,还会提高后者的觉悟。由于人们喜欢与收入相当者交往,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劳动力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与1964年一样高,在收入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将会多出10%,而收入较高的1/3只会多出3%。所以,工会运动的力量让美国政治的经济重心下移,这让民主党人获益良多。
总之,与之前的“长镀金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态势大大有利于实施促进收入均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激进举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国家的人反而被当成怪物。无选举权的移民劳工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阶层;南方有条件地暂时支持经济平等,只要这不转化为种族平等;强大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就这样恋着你
- 【文案一】 财经记者夏沐,高傲冷艳、双商碾压, 最近却被知情人曝出贪慕虚荣、势利拜金,只爱金融大亨纪羡北的钱。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夏沐呼了口气,她跟纪羡北这次是真的完了。 看到新闻后,纪羡北面色如常。 各媒体记者都在发信息问...
- 06-28
- 豪门蜜爱:帝少的绝色娇妻
- 被家人送上陌生男人的床,被交往的男友背叛,这一切她都忍过来了。可是当那个侮辱了她的男人大摇大摆出现在她眼前,要她赔偿的时候,她怒了! 她不就是一烟灰缸把他砸破相了,他至于不依不饶的吗? “当初打人的可是你。”他一脸的风轻云淡。 “当初...
- 06-15
- 首席医官
- 内容介绍: 挽救你的生命,即挽救你的政治生命。 机缘巧合之下,踏入了半官半医的“御医”之列。 在展现中医强大魅力的同时,曾毅也实现着自己“上医医国”的理想,一步步直入青云! 本书目前已经正式结册出版,出版书名改为《首席医官》,喜欢本书的兄弟...
- 05-31
- 怦然婚动:老婆高高在上
- 她,是处处受挤压的落魄千金。 他,是高贵不可亵渎的商界帝王。 两车相撞,他问的不是应该如何赔偿,而是直接问她:“想要结婚吗?” 婚后,他让她一三五随他扑倒,二四六陪在他身旁。 她再也受不了,拉横幅抗议:“还我自由,我要离婚!” ...
- 10-28
- 女总裁的全能兵王
- 为了男人的承诺,萧晨强势回归,化身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横扫八方之敌,谱写王者传奇! 他—— 登巅峰,掌生死,纵横世界,醒掌天下权; 泡美女,扩后宫,玩美无数,醉卧美人膝!
- 09-17
- 我的美女总裁
- 他,一介平民!却拥有世界上最神秘的身份!他,有过人的战斗技巧!却带着一帮贫民踏上了一条不归的征程!冷若冰山的美女总裁;清纯俏皮的可爱护士;成熟妩媚的市长夫人;绝世冷魅的美女杀手......四哥,他到底是个何等的英雄人物?! 第一章:夜里救了个美女 ...
- 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