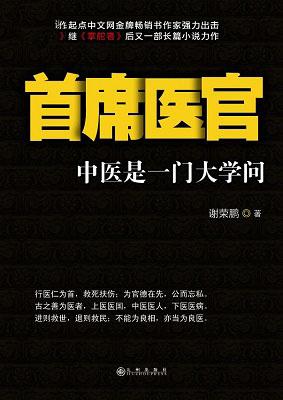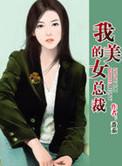第十三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1)(2 / 20)
为西部人虽然不矜不伐但也懒得检讨自己,检讨是一种人生体检,搞得好了可以两处得益,既发现了弱点也看到了特点,可惜他们不擅此道。有了这三点,西部人对自身的认识就难免糊涂,很难有一二三的列举、甲乙丙的说明。然而自觉的“列举说明”并不等于表达的全部,表达既可以是语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为和肢体的。他们可以不说却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自己仿佛领有使命般地通过举手投足把那种西部味儿浓浓烈烈地表现出来,表现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样充满了飙尘万里的苍凉和寄世人间的幸运。
197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右派陈源从祁连山深处的八宝劳改农场逃跑。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兴奋,面对茫茫原野,他顿时有了举足维艰的感觉:他从监狱来,他到哪里去?偌大一个世界,竟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顶着阳光照耀下的劳改犯的光头,穿着污迹斑斑的劳改犯的蓝色棉衣,标志鲜明地来到了祁连县城,目的似乎已经不是逃跑而是为了让人发现。但让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见他的人虽然都带着诧异的目光,却没有丝毫不友好的举动。他甚至在地质队的食堂门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个大馒头,又在县委招待所带火炉的门房里找到了暂栖一宿的床铺。就这样,在那么多温情的眼光绵绵不绝的关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连县城待了两天,然后向东而去。向东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风掀起后不知落往何处的尘埃,飘过了辽阔冷凉的俄博草原,飘过了茂密阴暗的仙米森林,飘过了水势盛大的大通河,飘过了冰天雪地的达坂山,最后飘到了西宁。漫长的两个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们的帮助,不仅没有挨饿受冻,而且有了一顶遮盖光头的皮帽子,换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劳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张望着省会的繁华拥挤时,他已经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罪孽”标记的劳改犯了。在西宁的日子里,他躲在先他释放的难友老贺家里,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两件大事,一是带着怨尤写出了自己的申诉材料,二是流着眼泪写完了一首酝酿了几个月的长诗:《悼念周总理》。他说:“老贺,借给我点钱,我的目标是北京。”老贺给了他三十块钱,他又一次飘走了。
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197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右派陈源从祁连山深处的八宝劳改农场逃跑。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兴奋,面对茫茫原野,他顿时有了举足维艰的感觉:他从监狱来,他到哪里去?偌大一个世界,竟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顶着阳光照耀下的劳改犯的光头,穿着污迹斑斑的劳改犯的蓝色棉衣,标志鲜明地来到了祁连县城,目的似乎已经不是逃跑而是为了让人发现。但让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见他的人虽然都带着诧异的目光,却没有丝毫不友好的举动。他甚至在地质队的食堂门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个大馒头,又在县委招待所带火炉的门房里找到了暂栖一宿的床铺。就这样,在那么多温情的眼光绵绵不绝的关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连县城待了两天,然后向东而去。向东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风掀起后不知落往何处的尘埃,飘过了辽阔冷凉的俄博草原,飘过了茂密阴暗的仙米森林,飘过了水势盛大的大通河,飘过了冰天雪地的达坂山,最后飘到了西宁。漫长的两个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们的帮助,不仅没有挨饿受冻,而且有了一顶遮盖光头的皮帽子,换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劳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张望着省会的繁华拥挤时,他已经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罪孽”标记的劳改犯了。在西宁的日子里,他躲在先他释放的难友老贺家里,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两件大事,一是带着怨尤写出了自己的申诉材料,二是流着眼泪写完了一首酝酿了几个月的长诗:《悼念周总理》。他说:“老贺,借给我点钱,我的目标是北京。”老贺给了他三十块钱,他又一次飘走了。
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就这样恋着你
- 【文案一】 财经记者夏沐,高傲冷艳、双商碾压, 最近却被知情人曝出贪慕虚荣、势利拜金,只爱金融大亨纪羡北的钱。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夏沐呼了口气,她跟纪羡北这次是真的完了。 看到新闻后,纪羡北面色如常。 各媒体记者都在发信息问...
- 06-28
- 豪门蜜爱:帝少的绝色娇妻
- 被家人送上陌生男人的床,被交往的男友背叛,这一切她都忍过来了。可是当那个侮辱了她的男人大摇大摆出现在她眼前,要她赔偿的时候,她怒了! 她不就是一烟灰缸把他砸破相了,他至于不依不饶的吗? “当初打人的可是你。”他一脸的风轻云淡。 “当初...
- 06-15
- 首席医官
- 内容介绍: 挽救你的生命,即挽救你的政治生命。 机缘巧合之下,踏入了半官半医的“御医”之列。 在展现中医强大魅力的同时,曾毅也实现着自己“上医医国”的理想,一步步直入青云! 本书目前已经正式结册出版,出版书名改为《首席医官》,喜欢本书的兄弟...
- 05-31
- 怦然婚动:老婆高高在上
- 她,是处处受挤压的落魄千金。 他,是高贵不可亵渎的商界帝王。 两车相撞,他问的不是应该如何赔偿,而是直接问她:“想要结婚吗?” 婚后,他让她一三五随他扑倒,二四六陪在他身旁。 她再也受不了,拉横幅抗议:“还我自由,我要离婚!” ...
- 10-28
- 女总裁的全能兵王
- 为了男人的承诺,萧晨强势回归,化身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横扫八方之敌,谱写王者传奇! 他—— 登巅峰,掌生死,纵横世界,醒掌天下权; 泡美女,扩后宫,玩美无数,醉卧美人膝!
- 09-17
- 我的美女总裁
- 他,一介平民!却拥有世界上最神秘的身份!他,有过人的战斗技巧!却带着一帮贫民踏上了一条不归的征程!冷若冰山的美女总裁;清纯俏皮的可爱护士;成熟妩媚的市长夫人;绝世冷魅的美女杀手......四哥,他到底是个何等的英雄人物?! 第一章:夜里救了个美女 ...
- 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