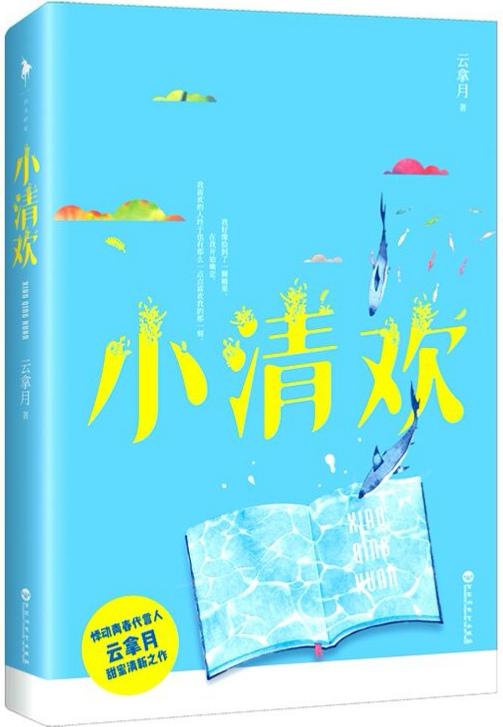第 1 部分(4 / 6)
,期待着我,我只有在重围中跋涉前行,日复一日顽强努力。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
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把它当做一束暗红的花,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等待他们在天上的阅读。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只知道我目前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因为,我已尽力。
毕淑敏
2007年1 月29日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
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
早上,发烧。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请病假吧。”
贺顿说:“跟谁?跟自己?”
柏万福说:“跟我。我安排来访者改期。”
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擦过咽喉。说:“不成。这关乎咱的信誉。”
柏万福反驳:“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
贺顿说:“我能行。”说罢,加倍服了退烧药,起床梳洗。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还特别施了脂粉。修饰一新,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
好在诊所就在楼下,交通方便。贺顿两膝酸软,扶着栏杆从四楼挪到了一楼。如果是挤公共汽车,那真要了命。
走进工作间,时间还早,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
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仿佛一只吸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正在打盹。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没有肛门,只吃不拉,因此腹大如鼓。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吞噬的是心灵猎物。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一半黏在沙发腿上,四分之一贴在天花板上,那些最诡异的故事,藏在窗帘的皱褶里。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它们就逃逸出来,一只翅膀耷拉着,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如同被藏匿的尸身,在半夜荡起磷火。
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贺顿觉得这不合理,衣服如同盔甲。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家就在楼上,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于是,她把几套常服,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上班的时候,如同武士出征,随心情挑选铠甲。今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下着灰蓝色的长裤。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谈话过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把它当做一束暗红的花,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等待他们在天上的阅读。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只知道我目前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因为,我已尽力。
毕淑敏
2007年1 月29日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
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
早上,发烧。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请病假吧。”
贺顿说:“跟谁?跟自己?”
柏万福说:“跟我。我安排来访者改期。”
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擦过咽喉。说:“不成。这关乎咱的信誉。”
柏万福反驳:“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
贺顿说:“我能行。”说罢,加倍服了退烧药,起床梳洗。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还特别施了脂粉。修饰一新,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
好在诊所就在楼下,交通方便。贺顿两膝酸软,扶着栏杆从四楼挪到了一楼。如果是挤公共汽车,那真要了命。
走进工作间,时间还早,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
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仿佛一只吸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正在打盹。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没有肛门,只吃不拉,因此腹大如鼓。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吞噬的是心灵猎物。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一半黏在沙发腿上,四分之一贴在天花板上,那些最诡异的故事,藏在窗帘的皱褶里。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它们就逃逸出来,一只翅膀耷拉着,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如同被藏匿的尸身,在半夜荡起磷火。
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贺顿觉得这不合理,衣服如同盔甲。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家就在楼上,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于是,她把几套常服,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上班的时候,如同武士出征,随心情挑选铠甲。今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下着灰蓝色的长裤。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谈话过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大奉打更人
- 《大奉打更人》1-12册实体书已在天猫、京东、当当全平台发售。 这个世界,有儒;有道;有佛;有妖;有术士。 警校毕业的许七安幽幽醒来,发现自己身处牢狱之中,三日后流放边陲..... 他起初的目的只是自保,顺便在这个没有人权的社会里当个富家翁悠闲度日。...
- 12-13
- 我只喜欢你的人设[娱乐圈]
- 作品简评: 因为一次现场“追星”,夏习清全凭一张脸红遍全网,也在当天被自己的爱豆戳破天使外表下的真面目,出场即翻车。一夜走红后的夏习清和偶像周自珩一起出演高难度密室逃脱真人秀,在烧脑游戏中针锋相对,在戏中戏的过程中接纳真正的彼此,撩拨与拒绝被撩的拉...
- 04-11
- 星汉灿烂,幸甚至哉
- 文案 许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觉得这辈子她投的胎实在比上辈子强多了,那究竟是什么缘故让她这样一个认真生活态度勤恳的人走上如此一条逗逼之路呢? 虽然认真但依旧无能版的文案:依旧是一个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长里短,细水流长,慢热。 天雷,狗血,玛丽苏,不喜...
- 04-12
- 大王饶命
- 灵气复苏了,吕树眼瞅着一个个大能横空出世。然后再看一眼自己不太正经的能力,倒吸一口冷气。玩狗蛋啊!……这是一个吕树依靠毒鸡汤成为大魔王的故事。
- 05-20
- 小清欢
- 全一中的女生都知道,乖戾嚣张打起架来不要命的第一名陈让,对隔壁敏学私立高中的齐欢没有半点好感。 只是那时她们不晓得,陈让自己也不晓得—— 在后来无数个躁动难安的夜晚里; 他会情难自抑地,肖想她一千一万遍。 **男女主双学霸/躁动小甜文...
- 04-13
- 初三的六一儿童节
-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帮派横行霸道,社会治安不良,警界暗藏腐败。著名的“三不管”地区蛟龙城寨(原型为九龙城寨)更是鱼龙混杂,驻扎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帮会。 骁骑堂的金牌打手夏六一,奉大佬之命,开电影公司洗钱。女主是大嫂,男主是被威胁的当红明星,导演...
- 07-13

![我只喜欢你的人设[娱乐圈]](https://www.wswxs.com/files/article/image/13/13271/13271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