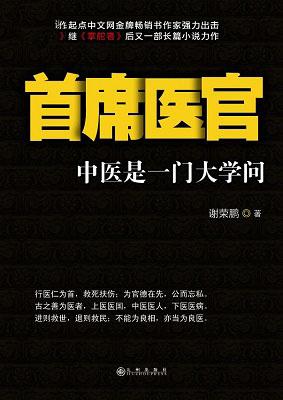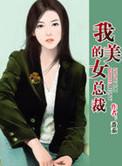第十六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4)(17 / 20)
,来到一片鲜嫩的牧地上,跳下马背,吆喝着驱赶那些先入为主的畜群。马上,几个牧人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双方对峙着,眼中都有凶光,谁也不肯相让,文登次仁和人家打起来了。
这就是草原上年年都会发生的草场纠纷。如果不是珠玛赶来,死命拽住丈夫,结果一定是动刀动枪,以死相搏。且不论这片草场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关心的是,以淳朴厚道为立身之本的草原牧家,为什么会对乡友邻人变得这样凶狠刻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使然。他们苦苦挣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牲畜繁育过多,草场严重超载,被采食过度的牧草失去了更新能力,草场退化了,迅速变成一片荒漠了。吃不饱肚子长不上秋膘的畜群,在冬春两季只能被冻死、饿死。死了再繁育,繁育了再死。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盲目发展牧业生产的恶果就是这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居守贫困、忍辱负重,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身上的衣服,变成生活的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精神的寄托才是永恒的追求,来世的幸福才是唯一的目标。由于对来世是否幸福的担忧和对今世还会遭罪的恐惧,由于担忧和恐惧的经久不散、镂骨铭心,他们对神灵的朝拜和生活一样绵长持久。只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无形中改变了朝拜的方式。二十一世纪初,珠玛一家又进行了一次艰难而神圣的远程朝拜。这次他们是去拉萨,是搭乘手扶拖拉机去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牧家都像珠玛一家这样用历史的沉默面对着现实骚动不宁的生活。在草原深处旅行,我们随处都可以觅到新文明的痕迹,草原给人的印象是那种沉甸甸的亢奋和哲人的洒脱——激越的藏族现代音乐,锦袍者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西装革履的人们粗犷的“锅庄”。剪毛房里,机声隆隆;羊毛从羊体上滚下来,堆在地上,须臾变成了一座小山;小山突然崩溃了,人们将羊毛抱进了打包机。卡车在公路上奔驰,上面装着整包整包的羊毛或者毛纺织品。药浴池边,牧人们拿着喷雾器,把圣水喷向羊群,涤除疾病。还有,改良羊、青贮窖、风能发电机、奶油分离器、人工牧草、优良的种畜场、灰色低矮却是文明象征的定居点,以及制止草场沙化的一次次行动——在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漠,人们采用围栏封育和人工种植两种办法,稳住了沙丘的流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牧草以每年平均十米的速度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就是草原上年年都会发生的草场纠纷。如果不是珠玛赶来,死命拽住丈夫,结果一定是动刀动枪,以死相搏。且不论这片草场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关心的是,以淳朴厚道为立身之本的草原牧家,为什么会对乡友邻人变得这样凶狠刻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使然。他们苦苦挣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牲畜繁育过多,草场严重超载,被采食过度的牧草失去了更新能力,草场退化了,迅速变成一片荒漠了。吃不饱肚子长不上秋膘的畜群,在冬春两季只能被冻死、饿死。死了再繁育,繁育了再死。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盲目发展牧业生产的恶果就是这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居守贫困、忍辱负重,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身上的衣服,变成生活的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精神的寄托才是永恒的追求,来世的幸福才是唯一的目标。由于对来世是否幸福的担忧和对今世还会遭罪的恐惧,由于担忧和恐惧的经久不散、镂骨铭心,他们对神灵的朝拜和生活一样绵长持久。只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无形中改变了朝拜的方式。二十一世纪初,珠玛一家又进行了一次艰难而神圣的远程朝拜。这次他们是去拉萨,是搭乘手扶拖拉机去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牧家都像珠玛一家这样用历史的沉默面对着现实骚动不宁的生活。在草原深处旅行,我们随处都可以觅到新文明的痕迹,草原给人的印象是那种沉甸甸的亢奋和哲人的洒脱——激越的藏族现代音乐,锦袍者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西装革履的人们粗犷的“锅庄”。剪毛房里,机声隆隆;羊毛从羊体上滚下来,堆在地上,须臾变成了一座小山;小山突然崩溃了,人们将羊毛抱进了打包机。卡车在公路上奔驰,上面装着整包整包的羊毛或者毛纺织品。药浴池边,牧人们拿着喷雾器,把圣水喷向羊群,涤除疾病。还有,改良羊、青贮窖、风能发电机、奶油分离器、人工牧草、优良的种畜场、灰色低矮却是文明象征的定居点,以及制止草场沙化的一次次行动——在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漠,人们采用围栏封育和人工种植两种办法,稳住了沙丘的流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牧草以每年平均十米的速度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相关小说
- 就这样恋着你
- 【文案一】 财经记者夏沐,高傲冷艳、双商碾压, 最近却被知情人曝出贪慕虚荣、势利拜金,只爱金融大亨纪羡北的钱。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夏沐呼了口气,她跟纪羡北这次是真的完了。 看到新闻后,纪羡北面色如常。 各媒体记者都在发信息问...
- 06-28
- 豪门蜜爱:帝少的绝色娇妻
- 被家人送上陌生男人的床,被交往的男友背叛,这一切她都忍过来了。可是当那个侮辱了她的男人大摇大摆出现在她眼前,要她赔偿的时候,她怒了! 她不就是一烟灰缸把他砸破相了,他至于不依不饶的吗? “当初打人的可是你。”他一脸的风轻云淡。 “当初...
- 06-15
- 首席医官
- 内容介绍: 挽救你的生命,即挽救你的政治生命。 机缘巧合之下,踏入了半官半医的“御医”之列。 在展现中医强大魅力的同时,曾毅也实现着自己“上医医国”的理想,一步步直入青云! 本书目前已经正式结册出版,出版书名改为《首席医官》,喜欢本书的兄弟...
- 05-31
- 怦然婚动:老婆高高在上
- 她,是处处受挤压的落魄千金。 他,是高贵不可亵渎的商界帝王。 两车相撞,他问的不是应该如何赔偿,而是直接问她:“想要结婚吗?” 婚后,他让她一三五随他扑倒,二四六陪在他身旁。 她再也受不了,拉横幅抗议:“还我自由,我要离婚!” ...
- 10-28
- 女总裁的全能兵王
- 为了男人的承诺,萧晨强势回归,化身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横扫八方之敌,谱写王者传奇! 他—— 登巅峰,掌生死,纵横世界,醒掌天下权; 泡美女,扩后宫,玩美无数,醉卧美人膝!
- 09-17
- 我的美女总裁
- 他,一介平民!却拥有世界上最神秘的身份!他,有过人的战斗技巧!却带着一帮贫民踏上了一条不归的征程!冷若冰山的美女总裁;清纯俏皮的可爱护士;成熟妩媚的市长夫人;绝世冷魅的美女杀手......四哥,他到底是个何等的英雄人物?! 第一章:夜里救了个美女 ...
- 06-30